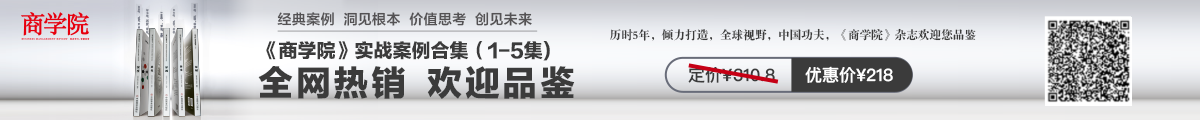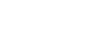用E-B-C范式破解“平台垄断”难题
原创 作者:刘青青 石丹 /
发布时间:2021-04-16/
浏览次数:0次

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在互联网时代,各“互联网巨头”几乎成为互联网领域的耀眼明星,也将影响力扩散到国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平台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掌握着海量数据和极高的市场集中度,主导着创新进程,但是也存在垄断、不正当竞争、遏制中小发展、侵害消费者、损害公共利益等乱象。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下称《指南》),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垄断的利剑正式举起。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原副校长)、原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于立指出,在经济概念当中,“数字经济”的提法要优于互联网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而“平台集团”更是反垄断中应当重点关注的概念。
因为“平台集团”是数字经济反垄断绕不过的难题,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深影响着反垄断的实施。其中,为了破解反垄断难题,于立还特别提出了E-B-C(Entity-Business-Conduct paradiym)范式在平台集团反垄断中的应用。
“解析”平台集团
而在于立眼里,要讨论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首先要定义的应当是主体,但看似独立分明的互联网平台背后也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联,给反垄断的定义和执行带来困扰。
也正是因此,于立提出了“平台集团”的概念,并将此作为讨论反垄断的重要一环。
据介绍,与大家熟知的企业集团类似,平台集团必然由多个平台共同组成,但平台集团也不是1+1那么简单的算数相加——集团内部的平台之间有乘法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互相依赖关系,也可能是竞争关系——互联网巨头多是非常复杂的盘杂交错的糅合。
于立认为,如果某个单一互联网平台存在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执行过程会比较简单.但如果是平台集团就会有诸多麻烦,要进行反垄断执法,按照实体定义,就要对其进行分解,分解到单一实体的范围,这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显而易见,当前市场提到的“互联网巨头”,几乎都是由多个平台共同组成的平台集团,而这些规模更大、能量更强的平台集团的监管,更是反垄断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那么,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平台集团的垄断责任要如何压实?于立认为,解析平台集团可以从“加总”或“分解”正反两个视角。就反垄断中“单一实体”原则而言,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分析:
纵向来看,平台集团与旗下平台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平台关系还是总分平台关系?又或者是两者结合的“树杈式”关系?其中是否存在独立平台或独立平台群?是否为单独上市平台?
横向来看,平台集团内部是否存在交叉补贴?对外跨界扩张时,有没有利用某一市场或某一平台的市场支配势力扩展到另一个市场,协助另一个平台?
于立指出,平台集团的基本特征是“一个集团、多个平台、多个市场”,同一个平台集团可以有多个平台实体,甚至多达十个、几十个,它们又分别介入多个业务市场,并且和数字经济有关系。因此,平台集团可以由无数个平台经营者组成,但不同平台经营者之间商业模式和经营行为各异,需要具体分析。
“所以,笼统地说哪个平台经营者如何涉嫌垄断,就对整个平台集团进行执法,那都是不准确的。”于立总结道。
用E-B-C范式破解难题
平台集团的复杂性不止于此,因为其规模与边界总是变化且模糊的,这也给反垄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可以想象,如果说平台集团外部是纯市场关系,同时单个平台内部是纯行政关系,那么集团内部的平台之间,则既有行政协调关系,又有市场交易关系。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台集团会自动追求最优规模。如果平台集团规模过小难则以实现“一体化经济”,规模过大又难以实现“专业化经济”,只能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调整。
用经济学术语说,只有当集团内部的边际协调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时,平台集团才能实现最优规模和最优边界。这背后的原因是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网络经济性。但这样一来,反垄断机构就必然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伴随规模经济的“赢者通吃”与垄断弊端并存的“两难抉择”。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既要允许平台集团实现最优规模和边界,又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平台集团如何审慎执法和司法,也就成了反垄断的世界性难题,于立指出。
就此,于立研究并提出了E-B-C范式,作为对平台(互联网平台或数字平台),尤其是对平台集团反垄断执法、司法的一种“三步走”分析思路和方法。
根据E-B-C范式,第一步,要先落脚于企业实体,对于平台或者平台集团,都要先分析其组织形式、组织关系,确定单一企业实体或者整个集团何者适用于《反垄断法》及《指南》。先按照单一实体将平台集团进行分解,然后进行责任承担。在单一实体承担责任的同时,还要分析研究其内部结构(如VIE架构等),进而落实责任人。
第二步,则要看业务类型,判断该业务类型是否与平台性质相对应。可能有的业务类型不是数字经济,还要进行相关市场理念的更新、界定。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进行分类施策原则,按基础设施平台、广告主导平台和一般应用平台,区别对待,分类适用。对基础设施平台应多予以支持鼓励,对一般应用应多包容审慎,只有广告主导平台才是反垄断执法重点领域。
第三步,考量经营行为是否需要豁免,这就涉及调查举证责任,垄断行为判定等,尤其是在EDA软件、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等新兴涉嫌垄断行为的判定,也有赖于反垄断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在处罚方面,集团的行为和单个经营者的行为和计算口径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判断垄断行为,还要研究处罚结构,而不是单一罚款或单一赔偿等等。不少涉嫌垄断违法行为身后都附加了赦免条款(正当理由),这不仅给垄断行为的判定留下了一片模糊地带,也给企业可能涉嫌垄断的竞争行为带来了斡旋的空间。
反垄断不是万能
平台集团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复杂难题,E-B-C范式也只是提供一个平台集团反垄断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放眼市场监管,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还存在不少法理概念需要澄清,执法程序、判定标准需要科学理性,执法与司法互补机制也有待完善。
于立认为,目前社会对《反垄断法》还存在一些误解。一方面,这些反垄断工作涉及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不是简单的一个指南、一个条规、一项案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民众希望通过反垄断法解决行政垄断,这是不现实的,那是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的,当下的可行途径是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一些企业比如实体书店,希望通过反垄断法要求其他竞争对手电商不降价,这种说法本身就涉嫌违法;还有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反垄断法保增长,那是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竞争政策见效慢、作用长,不适用解决经济过冷过热的问题。”于立表示。
但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竞争政策和反垄断必须分类施策,由行业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分类,由行业监管向重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与法院司法必须衔接互补。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指南》的出台确实为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给予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但也要注意和避免企业以反垄断诉求之名达到过反竞争之实。
需知,从中国《反垄断法》出台,乃至世界各国的反垄断实践当中,都存在着许多“反垄断悖论”的争议,例如“竞争者举报悖论”——同行越举报,说明越竞争;“共用品悖论”——共用品无垄断,有垄断的就不是共用品;“自然垄断悖论”——自然垄断无需限制市场准入,需要限制准入的不可能是自然垄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转化悖论”——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是选择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并实施普惠,而做到了这两点就变成了竞争政策……
毕竟,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地发展。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垄断,什么样的行为才会抑制竞争,什么情况下同样的行为又可能在抑制竞争和促进竞争之间徘徊转化……都值得细细推敲、字字斟酌。反垄断工作专业性很强,不应炒作成大众话题。
“总之,《反垄断法》实施不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反垄断也不是筐,有些不是反垄断问题,不能往里装,必须小心行政执法最后引起的行政诉讼。”还应该探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专业化、专职化,另外在司法系统设立反垄断法院的可行性。于立总结道。
除《商学院》杂志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商学院》杂志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
欢迎关注平台微信公众号

点赞 30
收藏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