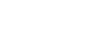前互联网时代,古人如何整合信息?

我读书的时候,还是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那时上网还要滴滴答答地拨号,谷歌、百度还没有普及,网上的消息更新得比手中的晚报还慢,老教授们站在讲台上,教我们如何使用索引书目,如何查四角号码,如何查期刊文章,如何查书籍版本,但还没等到我大学毕业,信息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再论述一个问题时,工作流程就变成了“搜论文—搜数据库—整合数据”,以至于今天的很多学术文章都被戏称为“关键词”文章。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搜索结果开始指数级增加,整合信息变成了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什么时候整合完成,工作才算大功告成。我们成了整理信息的机器,如果要做得好一些,过程中还需再进行一下辨别。所以当有一款程序不但能帮我们把相关信息搜索出来,还能将它们按照逻辑整合时,这款程序就代替了我们80%的工作。这种代替性让我们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和恐慌:我的电脑,它会自己写文章了!它知道的信息比我多得多,逻辑也通顺,甚至连一个错别字都没有!但我们暂时还不用对人工智能(AI)存有这么大戒心,因为它所做的不过是信息整合中的一小部分工作,而这部分工作在前信息时代更是初步。
现在我们将时钟倒拨,回忆一下在互联网、搜索引擎时代出现之前,我们如何整合信息?计算机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彻底代替人类呢?
类书:被整合的知识
类书的编制,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对ChatGPT模式的一个实践。
古人做学问的过程跟现代人差不多,都可以归纳为:搜索—整合—创新,只不过我们现在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在搜索和整合上,这反而影响了现代人对认知的进一步推进。我时常羡慕古代的文人,在信息有限的时代里,不管“经、史、子、集”哪一门类,知识都是“有数”的,花十年八年就几乎可以穷尽一个领域内的全部文献,有限的信息被梳理完成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和创新。而今,随着互联网、数据库、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掌握一个研究领域的所有信息,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我们把研究对象缩小到一个名词,也会有数以万计的信息朝你涌来,让你难以完全掌握既有信息,这就让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占尽先机,它借助强大计算基础上的搜索功能,进一步用人类的逻辑顺序整合了信息。
用惯了搜索引擎的我们,早已不记得前人是怎样了解世界了,甚至还会认为在没有谷歌和百度的时代,人们都是“博闻强记”,用“腹检”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也不尽然。虽然古代饱学之士读书多,记忆力也比常人要好些,但是他们在搜寻信息的时候,还是要靠工具书。
多年前曾有这样一则新闻,1981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访华,当时北京正值盛夏,卡特一下飞机就在“中国通”的指导下念了两句中国古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褦襶,意为不晓事)。这两句诗显然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词名句,但是被外国人随口吟出,中方接待人员却不知道出处,着实有些尴尬。当时没有搜索工具,最后文史专家翻了好一阵子,翻到《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才知道是晋人程晓所作的《嘲热客》。
实际上,这首诗应该是卡特的顾问们从类书里找的。打开唐代著名类书《艺文类聚》“伏”这一节,《嘲热客》就在其中。类书是指辑录各种典籍资料,分门别类以便检寻征引,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书籍。古代类书是文人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从魏晋六朝直至明清近世,历代类书的编纂绵延不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和历久弥新的修撰传统,同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类书的编制,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对ChatGPT模式的一个实践。类书的编纂者类似一个人工搜索引擎,将各种文献中关于某种事物的记述一一罗列之后,作者利用自己的基础知识对这些文献做简单的分辨和筛选,有时也会总结出自己的意见,以供他人翻阅使用。在古近代中国的知识世界里,官修类书往往以“御览”为动机,也就是为皇帝私人定制的“搜索—整合”系统。比如康熙皇帝尤其喜欢编纂类书,先后编敕《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子史精华》《骈字类编》等大型类书。同时期,清朝大臣陈梦雷在胤祉的资助下编纂《古今图书集成》,这是我国现存卷帙最多、体例最完备的类书。除了官修类书,宋元以降,渐次兴起了私修类书和坊刻类书,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备览”。从“御览”到“备览”,不仅反映出类书阅读主体的改变,更反映出知识受众的普及化。
奏折与邸报:古人如何收集政治信息?
无论是军机处对奏折的整理,还是各省驻京人员誊抄邸报,本质上都是对政治信息的搜集和整合,虽然耗时耗力,但是整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很高。
相比于学术信息,政治信息的收集对于古代人而言可能更为棘手。今天,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打开邮箱和信息传递工具,接收上级的指令、合作方的进展、同事和平行部门的告知,并给予相应回复。我们通常以为,这一系列信息流的传递和交互,无疑是要建立在完全现代化的手段之上的,但早在清代,这种分层次、分等级的信息流交互过程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完全畅通。
进入明清代之后,人口激增、国家地域扩张、战争规模扩大、经济行为复杂化、行政层级多元化,种种因素使得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必须更加全面而高效,皇帝的信息收集成为了头等大事,奏折制度也因此应运而生。
奏折是清代康熙末年开始实行的一种信息传递机制,本质上是皇帝收集各地、各衙门信息的手段。这种制度的设置,使皇帝变成了信息整合中心,在收到各种信息后,他要决定哪些信息交给哪个部门处理,在整理、辨别信息之后,分配知情权和处置权,而军机处就是协助皇帝搜集、整合信息的“智囊团”。虽然比起软件来,他们更慢,耗费也更大,却有两个突出的优点:第一,他们可以甄别信息来源的真伪;第二,他们会根据信息进一步给出处理建议。所以,如果不计算运营成本,军机处对于政治信息的处理和反馈能力,远在人工智能之上。
那么,地方官员又如何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获知中央的政治信息呢?第一种方式是私人打探。当时的官绅之间有着强大的关系网络,他们为了结识彼此,通常将个人信息编为《缙绅录》,以供查找和交互信息。在外地当官的官员也会派“家人”在省城、京城常住,为他们搜索政治信息。比如在唐代,就有进奏官为藩镇长官搜集各方信息,称为“进奏院状”。这种信息整合的目的主要为便于节度使了解形势后作出正确的判断,以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进奏院状的主要内容是:官吏的迁降任免、大臣的奏章上疏、皇帝的言行举动、朝廷的政策规章法令以及其他比较重要的政治事件。有时也会对藩镇长官特别感兴趣或和本藩镇关系比较密切的相关信息,进行较为连续和集中的记录。
第二种是一种公开传播的政治信息,就是“邸报”。当时各地在京城都设有办事处,称“邸”。驻京人员会定期把皇帝公开发抄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记录下来,由信使骑着快马,传送到各郡长官处。
无论是军机处对奏折的整理,还是各省驻京人员誊抄邸报,本质上都是对政治信息的搜集和整合,虽然耗时耗力,但是整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很高。
商书与商人会馆:怎么整合商业信息?
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不同地区间的价格差异是驱动商人往返各地贱买贵卖、赚取差额利润的原动力。
文人和官员都有自己搜集整理信息的渠道,那商人有没有这类渠道呢?显然,他们的信息搜集渠道更为通畅,来源也更多。中国幅员辽阔、山川纵横,自然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这使得不同地域的经济差异非常明显。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种不均衡发展在逐步扩大,表现也更为突出。地区性差异的存在和区域间互补性的经济流动,是封建时期商业发展的推动力。特别是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不同地区间的价格差异是驱动商人往返各地贱买贵卖、赚取差额利润的原动力。所以,对于商业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商人有着极大的内驱力。
传播商业信息最为公共的形式称为“商书”,是公开编写的从商经验。明清之时,商书出版尤其繁盛,它们从商人观点角度编写,天文、地理、朝代、职官,以及全国通商所经的里程道路、风俗、语言、物产、公文书信、契约、商业算术、商业伦理等无所不包。这类书的大量出版和一再刊刻反映了彼时商人对可靠知识和信息的大量需求。
第二个公共传播区域是酒楼茶肆等人员密集场所,在这些地方,商业行情和各种供求信息最为丰富。清代歙商张顺年少时随其兄出外做生意,在肆中,张顺“执勤不懈,百货心历,相时而消息之”(非常勤快,对所有货品心里都有数,并看准时机传播消息),如此“佐父起家为大贾”,可见在公共场所打探商业信息是清代商人的惯用做法。
私下传递商务信息最常见的方式是书信往来,商业繁荣地区都有极为密集的通信网络。以徽州地区为例,宋代徽州设有专送文书的省递35铺(驿铺,去称驿站),传送情报兼侦察、防盗贼职能的斥堠38铺。到清代,驿铺发展到县级,其中县驿6个,分布于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旌德县城内,并设急递铺94个,可见当时信息收集成本虽然高,但商人们仍大量投资于此。
另一个信息联络的常见方式是利用社会关系结帮经营,通过内部传递信息,实现行业垄断。比如在徽州一些竹枝词中写有茶商“去岁茶商得利丰,今年山价定然昂”,“侬家夫婿估浔阳,信报头茶已放洋。急急忙忙缘底事,山园又有子茶香”。学者研究称,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商业情报收集方式:一种主要用于晋商中,利用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分号设在外地重要城市;另一种是徽商,主要是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大商人常常借祭祀等机会召集在各地经商的族人集会,交流各种信息。至于众多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
商业信息大体有两种来路:一种是大路货,公开发布,类似今天我们在网上能够找到的信息;另一种是私货,需要个人去跑关系建立网络,在人际交往中获得。这两种信息,前者是基础,后者则是成功的关键。虽然现在的技术还不够发达,但也许终有一日,电脑可以帮我们全部完成“大路货”信息的整理工作,让我们腾出手来去获得能安身立命的“私家信息”。
对于我们已知信息的检索和集合,计算机确实已经超越了人类,现在它又学习了语言逻辑,并会按照合理的顺序来组合这些信息。不论历史还是现实,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进步,归根结底来源于对既有信息的分析和进一步的创新。举例来说,ChatGPT可以帮助本科生写作业,却无法帮助硕士、博士生完成全部研究。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指的是我们去研究。回头想想,AI能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帮到我们什么呢?
作者 | 王敬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古代 史博士,关注清代政治史、宫廷史研究)
除《商学院》杂志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商学院》杂志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
欢迎关注平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