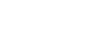人类起源,那些光怪陆离的传说
原创 作者:王敬雅 /
发布时间:2022-08-18/
浏览次数:0次

2022年10月3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奖项授予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以表彰他在人类进化以及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前不久,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证实人类是从鱼进化来的,从鱼到人演化过程需近5亿年,先后经历从最早的无颌类演化变成有颌类、肉鳍鱼类,之后登上陆地变成两栖类和哺乳动物,最终演化成人类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探索仿佛已经离答案越来越近。对于“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一问题的执着,其实植根于我们的天性,只是我们和古人的区别在于,现代人对人类起源的认知,是在科学性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严密推断,而古代人对于人类起源的探讨,则都是出于猜测和奇幻的想象。
这两种对于人类起源的探讨,表面上南辕北辙,毫无关系,而且古代人类起源的传说,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荒诞,但是在这些荒诞的故事背后,反映出的是人类的自我想象和史前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今天我们再来探讨这些传说,并不是想从中求得问题的答案,而是想透过这些问题,窥探我们的先民彼时的所思所想。而这些光怪陆离的传说,也是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最初的凝结力。
广为人知的神话:无性还是有性
虽然古人可以看到个体的人是代代繁殖生下来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相信,最早的人不是有性繁殖的产物,而是被神制作出来的,人与神有直接的创造和继承关系——人是神的子孙或者作品。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造人神话中基本都是“无性造人”。古人认为,造人和人类繁殖并不是一个事件,人是先被某种力量创造出来,然后再进行繁殖行为。在我们最熟悉的传说中,人的起源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女娲“抟土造人”。“女蜗”这个词最早见诸《山海经·大荒西经》。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在这里,经传只记载了女娲的肠子幻化为十个神人,而没有提到女蜗“抟土造人”的情节。后来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楚辞集注》中描述:“女娲人首蛇身,一日七十化。”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女娲是“古之圣女,化万物者”。
但这些记载都只描绘了女娲的外观形象和神异奇能,却没有涉及她“抟土造人”的事情。直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才谈道:“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解于泥中,举以为人。”这是关于女娲“抟黄土造人”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记载。正是根据这一记载,后来在民间经过口耳相传、加工修改,又创造了许多有关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
这些“人类来自泥土”的造人神话,在西方创世神话中也有体现。在德国作家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里,关于普罗米修斯造人是这样描写的:“(普罗米修斯)知道天神的种子蕴藏在泥土中,于是他捧起泥土,用河水把它沾湿调和起来,按照世界的主宰,按照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为了给这泥人以生命,他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了善与恶两种性格,将它们封进人类的胸膛里。在天神中,‘智慧女神’雅典娜惊叹于这一创造物,于是便朝具有一半灵魂的泥人吹起神气,使它获得了灵性。”
第二就是伏羲女娲结合生人说,唐代李亢的《独异志》中描述:“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
在希腊神话中,“大地之神”盖亚是众神之母,在天地开辟前,她由“原始神”卡俄斯身体内所生,她生下“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又与其结合生下了泰坦“神族”,所有的天神都是她的子孙后代。至今,西方人仍然常以“盖亚”代称地球。盖亚在西方神话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神话中的女娲,不同的是,女娲直接创造了人类,而盖亚则是先创造了众神,也可以说她是西方人类的始祖。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想象:虽然古人可以看到个体的人是代代繁殖生下来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相信,最早的人不是有性繁殖的产物,而是被神制作出来的,人与神有直接的创造和继承关系——人是神的子孙或者作品。这是早期人类一种认知的自觉性,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与其他的生物不同,他们是某种主宰者创制出来统治世界的物种,是神的意志最直接的继承者。
多彩的传说:卵生人、植物生人还是动物生人
母题实质上表现了一个人类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成为该群体的文化标识。
在介绍各种人类起源传说时,我们要谈谈“神话母题”这一概念,它指的是构成神话作品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能在文化传统中独立存在并被不断复制,虽然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构成无数的作品。比如同样是“抟土造人”这个母题,汉人传说中就是“女娲”,达斡尔族是“恩都力”,哈萨克族是“创世祖迦萨甘”。这些母题实质上表现了一个人类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也成为该群体的文化标识。
所以,虽然各民族有着不同的人类起源传说,但是母题的数量并不多,除了最常见的“泥土造人”“神造人”之外,还有“感生”“卵生”“植物生人”“石头变人”等二十余种。而且我们发现,越是地形单元复杂、民族杂居的地方,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就越多。
“抟土造人”是具有世界性的人类起源神话母题。目前已经发现于埃及、希腊、印度、巴比伦、希伯来、波利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南亚、非洲、北美洲,遍及了全世界。在中国各民族中,汉、壮、彝、独龙、佤、土家、蒙古、崩龙、傣、哈萨克等民族都有“泥土造人”的神话。
除了泥土造人,比较流行的还有“卵生人”和“植物生人”。“卵生人”的说法在喜马拉雅山一带的中国西藏、印度,东南亚各国,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地流行。《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我国的少数民族中,纳西族、苗族、畲族,以及骆越族群中的傣、侗、水、黎等民族也有此神话母题。
研究发现,卵生人神话与世界各地普遍流传的“宇宙卵”神话有密切联系,也就是指宇宙诞生之初,是一个混沌的“蛋”。人类学家们认为,这些神话应该与原始人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有关。在初民思考宇宙万物起源的过程中,他们观察到了各种鸟类和爬行类卵生动物的繁殖方式,所以可能进而推测,世间万物包括人类自己都是从“蛋”里面孵化出来的。
植物生人的例子就更多了。这种母题神话中生人的具体植物有树、叶、草、竹子、葫芦、水果、木头等等。比如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葫芦经常是孕育早期生命的载体。傣族的创世神话中,葫芦是已经神化了的灵物。在荒远的古代,地上什么也没有,天神见了,就让一头母牛和一只鹞子来到地上,母牛生下了三个蛋,鹞子来孵这三个蛋,其中一个蛋孵出了一个葫芦,人就是从这个葫芦中生出来的。
在云南基诺族的创世神话中,除了“葫芦生人”,还有早期文明中流行的洪水神话。故事说:在史前的一场大洪水后,只剩下一对孪生兄妹,这对兄妹结为夫妻后,神仙给了他们葫芦籽,葫芦籽种下后,结出了一个大葫芦。他们俩打破了大葫芦,里边走出了基诺、汉、傣等各族人民。拉祜族的创世神话也记叙了天神厄莎种葫芦创造了人类的故事。傈僳族中也流传着人类来自葫芦的神话,说是天神降下两个葫芦,第一个葫芦出来了男人西萨,第二个葫芦里出来了女人诺萨,他们生育了九男九女,互相结为夫妇,生出了汉、彝、缅、景颇、纳西等各族人民。
在先民众多的起源神话中,藏族的民族起源神话别具一格,甚至能看到现在的“进化论”的影子。在藏族人类起源神话中,人是猕猴变来的。例如成书于公元1388 年的《西藏王统记》中,就记载了藏族人种出自神猴与岩山魔女的神话。神猴在山中修行,遇岩山魔女请求与之结合,神猴不愿,岩山魔女使尽手段恳求它,神猴最终在观音菩萨的指点下与岩山魔女结合,并生下六只小猴,这六只小猴是由六道有情众生死后前来投胎的,后来繁衍成五百只小猴,得食香谷,逐渐演变成人类,成为藏族先民。我们会发现这些神话不仅是先民神话故事的产物,还进一步结合了后来的各种宗教传说。
此外,还有些母题是交叉结合的,比如“神造人”和“动物生人”“植物生人”可以结合起来。五帝之一、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她与别人外出洗澡时看到一枚鸟蛋,吞下之后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商人的始祖,这也就是《诗经》中描写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先民的思考:泥土还是神灵
神话作为当今人类可以追溯的最早的语言艺术,在人类文化的演进中发挥着重要的原型作用。
古代的人类,头脑里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在其意识、思维和心理中笼罩着神秘的色彩,显现出各种各样的“神的幻影”。此时人类心中是一尊尊崇拜的神,这既是他们探索宇宙奥秘、认识和理解大自然的思想基础,又是他们创作神话的思想基础。人类近代文明兴起之前,我们的祖先凭借着伟大的天赋和想象力,创造出了各种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字。
我们之所以走入先民的认知世界,总结和思考他们对于人类起源的认识,并不是其中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注意到神话叙事的功能。神话在人类早期生活中,是一种解释世界万物、生产生活的教科书,同时也与人类的宗教信仰、人生教化以及行为规范等生存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类起源的母题,本身就有图腾标示的功能,而图腾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心理现象,不仅是一个族体的重要标志,有时还带有祖先性质,认为族体与其具有血缘关系。在生产形态尚不发达的人类早期,这一心理表现为对周围自然界和特定信仰物的高度依赖,而这种对于同类事物的依赖,形成了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特性。
比如在西方的创世故事中,人和神会存在一段斗争和博弈的过程,而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都是顺应自然而非挑战自然而生的。与古希腊和希伯来的神话相比,中国女娲“抟土造人”也表达了中国人对土地截然不同的态度。《说文解字》中记载:“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吐”字本从土声,则为以子释母,可见土地在中国人眼中就是最大最坚实的支撑。而女娲、伏羲蛇的形象,也是贴地而行的生物,生命力顽强且繁衍能力强,代表着土地和孕育,其象征隐喻也表明了人与大地有密切的关联。
还有一些细节中,我们能看出中国与西方文明中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宗教思想。女娲造人是泥土成型便成人,没有单独赋予他们思想和意识的过程,而在希腊神话中,人类由雅典娜吹入灵魂,在希伯来神话中,人类是由上帝吹入生气。
可以看出,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认为灵魂与肉体是分开的,人性的善恶与智慧都是后天形成的。由于亚当的堕落,后世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希腊文化中,将灵魂与神捆绑在一起,更加强调灵魂是从神那里获得。所以西方文化中人死后或升入天堂,或坠入地狱。而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文化中肉体与灵魂是统一的,人死后也没有一个灵魂审判的过程。
神话作为当今人类可以追溯的最早的语言艺术,在人类文化的演进中发挥着重要的原型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而蕴藏在神话中人类起源的故事,或许不像科学发现的那样精密和准确,但却是一个民族在形成之初最早的共同想象。
鄂温克族的起源神话中,曾经有一个大地母亲的形象,在今天看来,仍然光彩熠熠。这个故事说:“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个白发老太太,她有个很大很大的乳房。老太太是抚育万物的萨满,人间的幼儿幼女都是由她来赐予的。”
除《商学院》杂志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商学院》杂志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
欢迎关注平台微信公众号

点赞 30
收藏 20